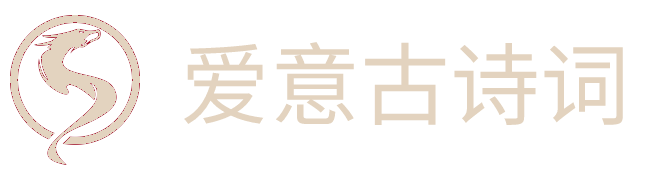岳飞,北宋抗金名将,被誉为“民族英雄”。然而,却在绍兴和议之后,被软禁并被处死。人们普遍认为,岳飞之死是由于金国对其威胁过大,必须除之而后快。然而,真正背后的原因却更为复杂。宋金绍兴和议,岳飞却非死不可的真正原因令人细思极恐。
宋高宗决心议和,为了避免手握重兵的大将岳飞和韩世忠等人反对,奸臣秦桧的党羽范“同献计于(秦)桧,请皆除枢府,罢其兵权。桧喜,乃密奏以柘皋之捷,召三大将赴行在,论功行赏”。三大将中除张俊因杨沂中、刘锜等都受他节制,还有“功”可言,至于岳飞、韩世忠则都与柘皋之战毫无关系,但都接到来临安朝觐的诏令,由于韩世忠、张俊驻地离临安较近,因而先期到达。岳飞驻地远在鄂州,接到诏书的时间较晚且路程亦远,到达临安的时间晚了七八天,这使得奸相秦桧担忧万一岳飞借故不来,阴谋便不能得逞,所以当岳飞一到,立即将随岳飞前来的幕僚朱芾李若虚派出任地方官,以免他们为岳飞出谋划策。
绍兴十一年四月下旬,宣布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张俊附和秦桧对金投降求和政策,数日后首先提出上交兵权,于是宣诏罢宣抚司,各宣抚司军官的官衔前都加“御前”二字,以示直属于皇帝,遂夺三大将兵权。六月,又派张俊、岳飞去镇江、楚州瓦解韩世忠的部队,虽然遭到岳飞的反对,张俊却收买了韩世忠部下总领财赋官胡纺,胡纺诬告韩世忠亲信将领耿著在楚州“鼓惑总听”,意在生事,耿著随后被逮捕,刺配远地。秦桧、张俊可能意在由此加害韩世忠,但韩世忠在建炎之初“苗、刘之变”中,对高宗有救驾之功,或许由于高宗的庇护才未被深究。
由于岳飞在对待韩世忠问题上与张俊意见不合,实际上即是违背了秦桧的意志,回到临安后随即被罢除实权。七月间只派张俊前往镇江措置军务,谋害岳飞的活动即是在镇江的张俊策划下进行的。八月初,岳飞被迫辞官赋闲。金,除非另一方面,金朝实际掌权者兀朮(宗弼)也感觉到消灭南宋已无可能,另立傀儡又不足以抵挡南宋的攻击,迫使南宋臣服看来是唯一可能的结局。
随后,金兀朮遂放回以前扣留的宋使莫将、韩恕,实际上是在向南宋示意可以降附。所以,当宋高宗得知此事,即认为“敌有休兵之意”。二人带回的信中,首先扬言要进行军事威胁,但接下来即称“义当先事以告,因遣莫将等回,维阁下熟虑而善图之”,这是没有先例的,胁降之意显现于字里行间。高宗心领神会,随后即派刘光远、曹勋出使兀朮军前,并回信说上次抗金之战,南宋“将士临危,致失常度,虽加诛戮,有不能禁也”,这一方面是对宋军打败金军表示歉意,另一方面是说如果金军再次南侵则只有抵抗一途,最后请求兀朮对南宋“曲加宽宥,许遣使人请命门(阙)下”求和。
金兀朮在十月初由宋使刘光远带回的信中说宋高宗“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讼,则当遣尊官右职、名望夙著者持节而来议和,即是说刘光远等地位太低,不能担任谈判代表。十月中旬,宋高宗改派吏部侍郎魏良臣为金国禀议使担任议和谈判代表在致金兀朮(宗弼)的信中除提出金应休兵以便进行和谈外,并声明:“专令(魏)良臣等听取钧诲,顾力可遵禀者,敢不罄竭以答再造”之恩,表明髙宗屈膝臣属的诚意,这次和谈取得了初步成果。十一月初金兀朮(宗弼)派萧毅来南宋以最后确定议和条件,并在来信中说:宋高宗“自讼前失,今则惟命是听”。并说:“本拟上自襄阳,下至于海为界”,“重念江南凋弊日久,如不得淮南相为表里之资,恐不能国,兼来使再三叩头哀求甚切,于情可怜,遂以淮水为界”,“来使云: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这实际上是将已在南宋手中的淮南恩赐”给南宋,还要南宋称臣纳贡。又说:“其间有不尽言者口授(金使萧毅),惟(高宗)详之。”
宋高宗、秦桧在与金和谈的同时,迫害岳飞的阴谋也在加紧进行。秦“桧与张俊谋杀(岳)飞”,“诱(王)贵告(岳)飞,贵不肯”,张“俊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秦桧又指使他人令王俊告张宪。绍兴十一年九月上旬,王俊即向都统制王贵告发副都统制张宪想据襄阳谋反,王贵即据以向张俊报告,当张宪到达镇江向张俊报告军务时即被捕,随后被送往临安大理寺狱。岳飞、岳云父子也因而被捕入狱。御史中丞何铸进行审讯,却“阅实无左验,(何)铸明其无辜”,于是秦桧等改命万俟(音“莫其”)离进行审讯,然而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
但是,金都元帅兀朮(宗弼)给秦桧的信中说:“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岳)飞,始可和。”因而当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南宋与金签订和议以后,岳飞遂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同年十二月末被害于大理寺狱中,张宪被判处绞刑,岳飞长子岳“云坐与(张)宪书,称可与得心腹兵官商议”,其罪“为传报朝廷机密事,当追一官罚金”,即只是降一官及罚金的罪,但宋高宗竟命杨沂中将岳云与张宪一起处于斩刑。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订立的和议,史称“绍兴和议”,以准河为界,将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割属金;南宋每“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给金。绍兴十二年三月,金派刘答为江南册封使,九月到达南宋京城临安,册文称:“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答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南宋在比金强,至少是军力相当的情况下求和。正如南宋理宗时学者吕中在《大事记》中所说:“向者战败而求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向者战败而弃地,今则战胜而弃地矣!”
宋高宗之所以如此屈辱地向金称臣求和,实际上是私心作祟,是怕金朝放出宋飲宗作为傀儡来与他抗衡,因而影响到他帝位的稳固。正如金兀朮(宗弼)数年后临死前“遗言”:“如宋兵势盛”,“若制御所不能,向与国朝计议,择用智臣为辅,遣天水郡公(赵)桓(即宋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宋高宗如此卑劣的思想当然不能公开表述,他公开表白的是:“若归我太后,朕不惮屈己与之和,如其不然”,“朕亦不惮用兵也”。绍兴十二年八月,高宗生母韦太后及徽宗等灵柩到达临安,宋金划分陕西边界也已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