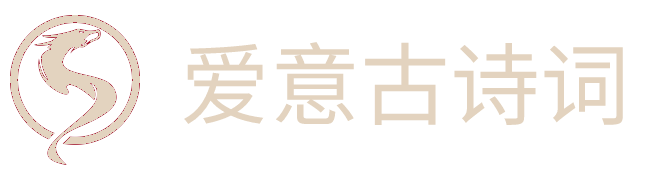当谈及孝顺时,人们总会想起朱逢博,他独守骨灰盒14年,守护着他逝去的儿子。这种无尽的悲痛在他心中蔓延,如同一根刺刺在心间,永远无法摆脱。儿子的离去,让他的生活变得无比空虚,只有在每天对着骨灰盒聊天的时刻,他才感到那一点点慰藉。朱逢博所展现出来的坚强和毅力,深深触动了人心,让人们感受到了孝道的真谛。
在八十年代歌坛中流行“南朱北李”这样一句话。朱是指朱逢博,李是指李谷一。
而李谷一却说:“我远远不如朱逢博姐姐唱得好,她唱主角的时候我还是个拉幕布的小配角。”
如果没有朱逢博,谷建芬和李谷一可能无法拥有今天的成就。

朱逢博为中国流行乐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白毛女》、《满江红叶似彩霞》、《请茶歌》、《金梭和银梭》等经典歌曲都是由她演唱的。
她被观众称为“东方夜莺”,是无数歌唱家心中的偶像。
可就是这样一位乐坛领军人物,晚年生活却让很多观众感到心疼。
她独自一人守着骨灰过了14年,其中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01
1937年出生的朱逢博,从未想过将来要当歌唱家。
她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是业内知名的建筑师。
受家庭环境的熏陶,朱逢博自幼爱读书,爱文学,更热爱中国古典建筑。
当时她的梦想就是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建筑家。
从未想过从事音乐道路。
后来朱逢博如愿考到上海同济大学。
在建筑系整整攻读了6年。
1960年,朱逢博被分配到上海历史纪念馆工作。
如果不是因为一次演出,
她将来有可能成为像林微因一样的才女。
只不过,命运的转折点就在此刻悄然降临。
有一次上海歌剧院来工地上演出。
纪念馆的同事们纷纷上台表演节目。
朱逢博也在大家的鼓励下登台演唱了一首歌曲。
嗓音清澈嘹亮,爆发力十足,非常有音乐天赋。
唱完后,上海歌剧院领导对她印象十分深刻。
于是,歌剧院领导把朱逢博调进歌剧院。
刚到歌剧院的朱逢博十分自卑。
她觉得自己是“半路出家”,从来没有学过声乐。
而歌剧院的同事都有一身童子功。
可耐不住朱逢博长了一副“老天爷追着喂饭”的好嗓子。
领导实在不忍心错过这样一位人才。
便把她送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几个月。
进修回来就直接让她担任剧院主演。
朱逢博璀璨的艺术人生,也由此拉开帷幕。
在歌剧院工作的那几年,朱逢博演唱了《刘三姐》、《嘉陵江怒涛》、《红珊瑚》等经典歌剧。
在领导眼中,朱逢博简直就是拥有“银铃般”的天籁之音。
团里把她当做重点对象来保护。
每逢演出,都会有一名领导亲自护送她。
为防止朱逢博因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分心,
领导三番五次在她耳边提醒:“朱逢博,你30岁之前不可以谈恋爱,更不可以结婚。”
那时候朱逢博是上海滩的“红人”,
爱慕者层出不穷,无一不被她的才华所着迷。
为避免这些男同事和朱逢博接触。
歌剧院安排四个女同事跟朱逢博睡在一间宿舍里。
工作期间女同事全程陪同在她身边,男同事无法对她进行干扰。
放假的时候团长还把朱逢博接到家中,或者让队长亲自盯着她。
让她完全没有谈恋爱的时间,更没有认识异性的可能。
由此可见,当时朱逢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02
不过千防夜防,“家贼”难防。
领导怎么也没想到,朱逢博竟然爱上了自己的老师施鸿鄂。
虽说是老师,其实施鸿鄂也就比朱逢博年长3岁。
不过施鸿鄂是正经科班出生的美声歌唱家。
自幼留洋海外,学习了正统的意大利美声唱法。
还在多场国际古典声乐比赛中,为我国赢得荣誉。
用“年少成名”来形容施鸿鄂一点都不为过。
载誉而归的施鸿鄂在歌剧院就像男版“朱逢博”一样,备受领导关爱。
也是很多女青年心中的“白马王子”。
朱逢博也不例外。
少女的心中总是对“白马王子”充满崇拜。
她很欣赏施鸿鄂的美声唱法,
可自己只会普通的民族唱法。
所以她绞尽脑汁想从施鸿鄂那里取取经。
只要施鸿鄂一开课,她就搬好凳子拿好笔记本去旁听。
可只要是施鸿鄂开课,整个走廊都挤满了人,想挤进教室都困难。
朱逢博心想,要是一直和大家一样在底下旁听,那何时才能让施鸿鄂注意到自己?
于是,她打算“剑走偏锋”。
她上课的时候不来,等施鸿鄂下课的时候再来。
施鸿鄂本来在琴房休息,但面对朱逢博的请求,他也不好意思拒绝。
于是私下里他也会给朱逢博补课。
不过施鸿鄂没有过多关照她。
只是让她自己弹着琴试唱几句,然后他就端着水杯离开教学楼了。
朱逢博以为施鸿鄂只是去水房打水。
结果过去两个小时他都没有回来。
就这样,一上午过去了。
施鸿鄂才端着水杯缓缓走进来。
他看着眼前还在练习发声的朱逢博很是惊讶。
本以为这个姑娘会因为自己的冷漠“知难而退”。
可她却没有任何情绪,甚至没有一句埋怨。
若无其事地问:“施老师,您回来了?那您教我唱歌吧。”
见朱逢博一点脾气都没有,施鸿鄂也瞬间没了气焰。
只好答应在业余时间给她补课。
不过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相差太大。
再加上朱逢博本就不是科班出生,基本功差太多。
每次施鸿鄂让她用“咪咪吗,吗吗咪”来练习发声时,她都唱不好。
第一句一出来,施鸿鄂就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
只能端着茶杯,叹着气走出教学楼。
一走又是两个多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朱逢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练好发声。
久而久之,施鸿鄂和朱逢博竟然培养出了感情。
但谁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那个年代人们思想单纯,感情纯粹而美好。
只是默默欣赏对方,并不急于确定关系。
1967年,朱逢博终于30岁了。
终于达到领导给她规定恋爱的界限。
心中压抑的感情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
她一刻也不想再等。
于是主动写了一封告白信给施鸿鄂。
那天施鸿鄂骑着自行车路过传达室。
他和往日一样,停下车子去翻阅当天送来的报纸。
其中有一张报纸上放着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施鸿鄂收”。
正文只有一句话:
“今晚十一时在排练厅楼梯口等我”。
署名只有一个“朱”字。
顿时间,施鸿鄂心里犹如“翻江倒海”一样慌乱。
一向镇定自若的他,在此刻竟然有些不知所措。
而另一旁的朱逢博又何尝不紧张?
她在镜子前一遍一遍的梳着头发, 一遍一遍的整理白色连衫裙。
想在晚上以最漂亮的形象去赴约。
施鸿鄂也回到房间反复梳理头发。
等到夜深人静时,两位各自从宿舍里向排练厅走去。
那晚的上海刚刚下过一场雨,
气氛似乎有些浪漫。
当施鸿鄂走进楼道的时候,
朱逢博已经在楼梯口等候。
还没等他开口,
朱逢博便说:
“我已经决定八月一日和你结婚,这就是我今天约你来的目的。”
说完这句话,朱逢博哭着跑出走廊。
施鸿鄂来不及回应,就被女孩这两行热泪打动。
六天后,也就是1967年8月1日。
朱逢博与施鸿鄂在上海一家小弄堂里举行婚礼。
一位是赫赫有名的歌剧女演员,一位是海归男高音。
在外人看来这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然而他们的婚礼却格外“寒酸”。
婚房只有10平米,还是单位借给他们居住的。
屋子里只有一张钢丝床,还有一个不知从哪里淘来的破旧书架。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家具。
丝毫看不出这是一间婚房。
只有大门口贴了一张囍字。
到场的亲友只有10位,互相寒暄几句便离场了。
婚后朱逢博的歌唱事业蒸蒸日上。
她与施鸿鄂亦师亦友,携手共进。
在丈夫的指导下,她为音乐界留下了很多经典形象。
《白毛女》中的喜儿就是一代观众心中的记忆。
《喜儿哭爹》更成为经典中的经典,也是后人无法逾越的一座高峰。
之后的几年,朱逢博带着上海歌剧院和上海芭蕾舞团,在国内国外参加了上千场演出。
她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将歌声送到祖国每个角落。
此外,朱逢博还翻唱专辑《蔷薇处处开》。
专辑中就有那首“红极一时”的《橄榄树》。
这张专辑在当初卖出300万盒。
属于一大销量神话。
而朱逢博没有选择和邓丽君一样成为歌星,赚得盆满钵满。
反而着力于音乐教学,为我国培养更多热爱音乐的学子。
与此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歌唱家。
她还在国内开设“朱逢博艺术学校”,
这在当时起到一个“开天辟地”的带头作用。
李谷一、谷建芬等人均受过她的指导。
受朱逢博的影响,谷建芬也将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
创办了“谷建芬声乐中心”,免费教老百姓唱歌。
其中毛阿敏、那英、刘欢、解晓东、孙楠、苏红、万山红、汪正红、蔡国庆等人都是谷建芬的弟子。
后来谷建芬还被乐坛称为“流行音乐教母”。
如果没有谷建芬的教导,流行音乐不会发展这么快,也不会涌现出像毛阿敏、那英等这么多优秀的流行乐歌手。
只不过,在成为“流行音乐教母”之前,谷建芬经历了很长一段的低谷时期。
外界对她的音乐风格均持反对态度。
她一度怀疑自己的流行曲风是不是正确的。
甚至萌生退出乐坛,不再继续音乐道路的想法。
关键时刻,朱逢博停下手中的工作,来到谷建芬身边开导她。
劝她坚持自己,不要放弃,并对她给予厚望,让她将流行乐传承下去。
在与朱逢博推心置腹的交谈中,
谷建芬大受鼓舞,并对她十分感激,从此在心中一直将她视为恩师。
后来,谷建芬专门为恩师写了一首歌《那就是我》。
这首歌也成为朱逢博音乐生涯中广为传唱的代表作之一。
彼时,李谷一的气腔唱法也进入瓶颈期。
外界的声音让她一度丧失信心。
朱逢博听闻,专程去北京看望她。
两个音乐人互相探讨,互相鼓励。
朱逢博的到来,对李谷一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犹如春风化雨般温暖。
李谷一 朱逢博
得到朱逢博的认可后,李谷一坚定地按照自己的音乐风格走下去。
此后,每到逢年过节,李谷一都会带上礼物去拜访朱逢博。
朱逢博、李谷一、谷建芬也被乐坛称为“中国乐坛三大女艺术家”。
03
1985年上海轻音乐团成立。
朱逢博担任首任团长,肩负起从全国各地挑选有天赋的音乐学子来进修的责任。
其中嗓子不错,外形也不错的学子,她也会将他们培养成演员。
最近在《披荆斩棘第二季》上大热的林峰就是朱逢博的学生。
随着音乐市场的逐渐进步,观众们接受阈限也渐渐打开。
乐坛中出现“百花齐放”的盛世。
朱逢博和施鸿鄂也开始合体登台表演。
将民族唱法和美声结合,非常具有巧思。
这对伉俪在音乐的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成就。
分则各自为王,合则天下无双。
为乐坛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夫妻二人出道半个世纪,始终坚守初心,兢兢业业为艺术奋斗,没有半点绯闻。
朱逢博还获得十大女高音歌唱家,艺术家终身成就奖等奖项。
被国内外称为“东方夜莺”,“中国的夜莺”等美誉。
2000年,63岁的朱逢博宣布退居幕后。
将机会留给后人,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培养新人上。
为艺术奉献大半个世纪的朱逢博,也终于有时间和丈夫静静享受生活。
夫妻俩牵手去买菜,牵手漫步在林荫小道中。
平淡而又珍贵。
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
2008年,施鸿鄂突发心脏病离世,享年74岁。
那一年朱逢博71岁,刚刚步入古稀之年。
朱逢博一时间无法接受丈夫离世的消息。
更无法接受未来的人生中没有丈夫的陪伴。
她不知道自己在家中该如何生活。
也不忍心让丈夫独自葬在冰冷的墓地里。
于是,她将丈夫的骨灰带回家,摆在客厅桌子上。
每天都会给丈夫擦骨灰盒。
吃饭的时候也会习惯性的拿两个碗。
一个自己用,一个摆在丈夫骨灰盒前。
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朱逢博从没有遗忘过丈夫。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丈夫似乎一直在她心中,从未离去。
朱逢博和施鸿鄂有一个儿子。
只不过儿子没有继承父母的音乐天赋,
夫妻俩从小就看出来他的嗓子不适合学音乐。
所以尊重儿子的选择,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业。
年轻时,朱逢博忙于工作,对孩子的陪伴少之又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儿子不知道妈妈是谁。
儿子这句话,也成为朱逢博一生的痛。
直到现在,她对儿子仍然心中有愧。
好在儿子慢慢长大,渐渐体谅到父母的不易。
他长大后成为一名程序员,现在还开了自己的公司。
不过因为工作繁忙,大多数时间都是母亲独自生活。
如今朱逢博已步入耄耋之年。
精神依旧饱满,坚持独立生活,自己买菜做饭,不想麻烦孩子和保姆。
每次出门都会精心挑选服饰,只要穿裙子就会配上一条精致的珍珠项链。
美人在骨不在皮,岁月偷走了她的青春,但没有偷走她骨子里的气质。
年过80岁的朱逢博,优雅高贵,依旧是街头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019年,82岁的朱逢博和75岁的李谷一登上东方卫视晚会。
两位义结金兰的姐妹,一见面就抱在一起抹眼泪。
李谷一说:
“我和老姐姐年轻的时候感情就特别好,现在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说完这句话,李谷一就扭过去抹眼泪。
两位老姐妹的对话,让很多观众潸然泪下。
李谷一和朱逢博也是继郭兰英之后,首次将中国民歌融入通俗唱法的艺术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她们的出现启发了一代音乐人,
或许她们终将老去,但她们的歌声会永远回响在乐坛当中。
今年朱逢博老师已经85岁高龄。
因为患有糖尿病,需要长期吃药治疗,行动也有些不便。
不过儿子已经搬到母亲楼上居住。
平日里各自生活,儿子会定期带小时工去家里帮母亲做家务。
朱逢博一生乐善好施,与人和善。
附近很多同龄人都是她的歌迷。
知道她行动不便后,歌迷们轮流去家里陪她聊天,陪她沐浴阳光。
只不过,她最多的时间还是在家里看丈夫的遗像。
她也不愿意让儿子在家里过多停留。
朱逢博更多的时候是独自对着丈夫的骨灰盒说话。
或许,丈夫的离去她还未能释怀。
其实回首朱逢博和施鸿鄂的爱情故事,并不浪漫。
从告白到结婚,仅仅6天时间。
他们没有约会,没有像其他情侣一样在月光下散步,在公园里徜徉花海。
没有任何浪漫宣言以及海誓山盟,就直接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可当岁月的急流涤荡尽世间的繁华,
留下的是洗尽铅华的真情。
这对伉俪,并肩同行半个世纪。
完美诠释一生一世一双人。
为艺术奉献一生,为推进音乐事业奉献一生。
他们的歌声唱尽人间真情,道尽人间真爱。
亦师亦友,亦是人生路上不可多得的知己。
距施鸿鄂离世已经过去14年了。
她始终守着丈夫的骨灰盒,与他进餐,与他对话。
这样深情默契的夫妻之情,不禁让人泪目。
宋代文学家晏殊有一句词,或许可以用来形容朱逢博对施鸿鄂的感情: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